编者按: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支菲娜自2021年起,每逢春节档结束后便会在第一时间接受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盘点去岁电影市场问题,分析今次春节档得失,并对新的一年电影市场做出展望。
专访以上、下两篇的形式刊发,本文为下篇。
【对话】
不改革就是等死,分线发行势在必行
澎湃新闻:2024年,中国电影遇到了不少挫折,你观察到行业做了哪些自救或者创新措施?
支菲娜:我可能比其他学者更关注管理层的动向。2024年年中,指导电影管理的大方向出现了一些变化,电影进一步向内求改革。我的观察是,管理层比往年更多地加强行业内部交流、更多地走进剧组鼓舞人心、更多地深入城市农村市场调研。在着力提升创作质量之余,也创造了一些新玩法,来激发电影的活力、吸引年轻观众的注意力。
2024年2月到2025年1月,管理层推出了“电影+金融”,联合央行数币所、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联,从发放惠民消费券入手,推动更广范围的金融合作,引入金融活水,逐渐打破金融与电影“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这一活动也得到了地方管理部门和金融业的积极响应。希望今后金融能改变中国电影上游资金池和自有资金池面临枯竭的情况。
2024年6月16日,管理层推出了“电影+邮政”,把广为人知的“龙标”印上了邮票,片方和观众还可以花很少的钱在该邮票副票上印上指定图案,获得专属“龙标”邮票。虽然只是区区面值1.2元的邮票,但“龙年+龙标+616”这么“6”的小产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普通人对“龙标”的刻板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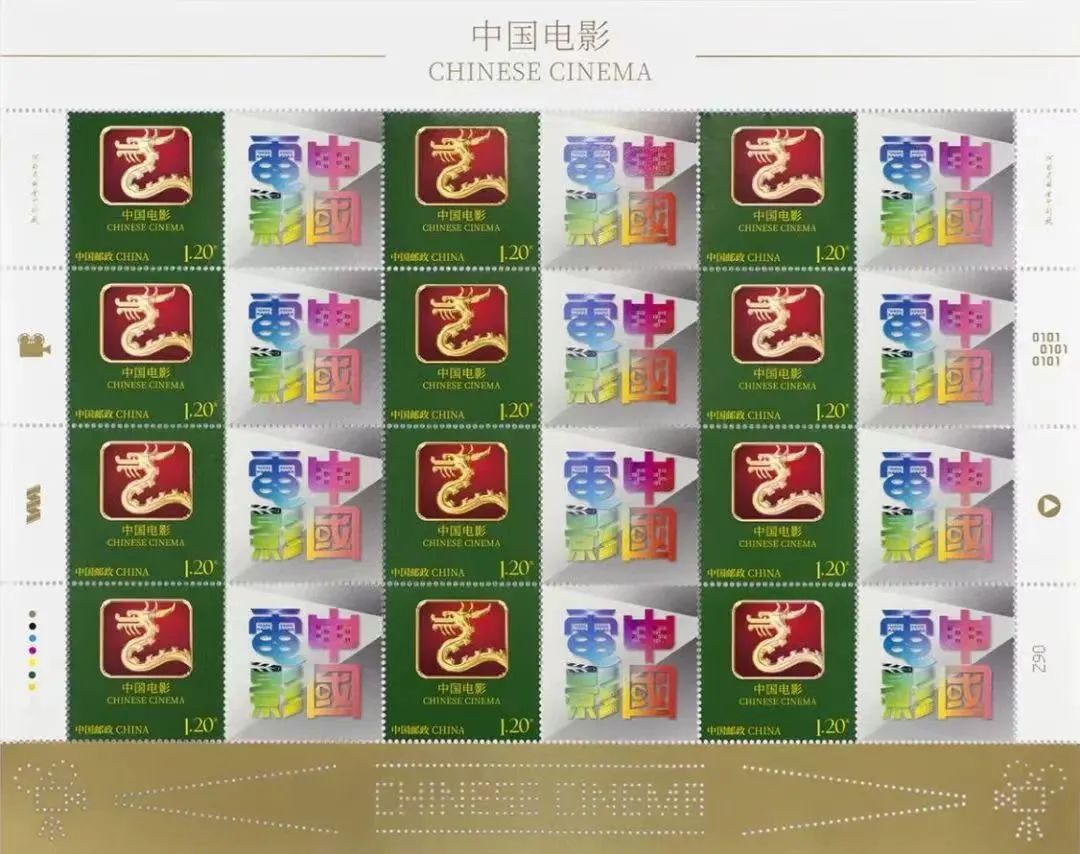
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正式发行的《中国电影》个性化服务专用邮票
2025年1月,管理层推出了“电影+美食”活动,让餐饮企业和电影企业联手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的促消费活动。随后又在《唐探1900》的外景地推出了“电影+旅游”活动,引导观众“跟着电影去旅游”,全国多地凭电影票可以享受门票打折。可以说,对于老百姓而言,电影不仅要好看,也要好吃、好玩,如果还能薅羊毛,那就更好了。
澎湃新闻:除了你说的这些管理层的创新,业界的改革动力如何?你提到分线发行,过去一年的效果怎么样?
支菲娜:2023年10月,业界开始探索分线发行。新鲜事物难免会走弯路,所以咱们在2024年春节档的访谈时,我才会说“瓜分市场不是分线发行”。一年来,质疑、嘲笑、哭诉、抵制,什么声音都有。但走到2024年下半年,大家都明白了,不改革就是等死,分线发行势在必行。
我们看到,一些小众影片采取了一家影院长期放映的方式,比如《康熙与路易十四》;一些经典影片只选择高品质影院放映,比如《哈利·波特》全系列重映只在3000多家影院举行;一些影院尝试放映演唱会的影院版,比如2023年12月31日开启的《泰勒·斯威夫特:时代巡回演唱会》,还有《皇后乐队蒙特利尔现场演唱会》《张杰曜北斗巡回演唱会》等等;一些影院甚至开音乐会、直播电竞总决赛、打《黑神话·悟空》游戏、办电视剧线下宣传活动。效果好不好,市场最知道。
分线发行的实质是精细化多样化发行,让那些个性化的影片、影院和观众互相找到。重磅节目不够多的时候,需要灵活经营、先活下去。今年还会继续探索。
回到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初心
澎湃新闻:坚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智慧。去年暑期档除了《抓娃娃》一枝独秀,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进口影片《异形:夺命舰》会成为这个档期末尾最大的黑马。当然,不止这一部影片,我也注意到去年有多部影片上映时,影院或者宣发都打出了“18岁以下的观众应谨慎选择观看”的告示,但这并没有妨碍它们目标受众的观影热情。
支菲娜:2024年,进口电影延续“多国别、多样化”的方针,基本网罗了全球高票房、高口碑且重视中国市场的优秀影片。同时,在我看来还是有三个明显变化。
一是数量有明显恢复。2024年有76部进口影片进入市场,加上11部中国香港影片、10部中国台湾影片是按照进口影片渠道进入内地市场的,所以一共有97部进口影片,高于2023年的91部、2022年的62部、2021年的80部。
二是进口影片的结算票价提高了,也就是说进口影片在中国市场的最低售价提高了。所谓结算票价,或叫保底发行价,是指电影放映方(院线、影院)和电影片方(制片、宣发)最低按照哪个价格结算。
长期以来,出于保护国产影片的原因,进口影片的结算票价都低于国产影片。比如《阿凡达:水之道》这样的国际顶级制作,结算票价也只有25-30元。而一众国产中小成本影片的结算票价都在30元以上,不少大档期影片甚至高达55元。而2024年1月,美国B级片《养蜂人》调高了结算票价至30-40元。这一变化既显示了中国电影市场发展成熟后的包容心态,对进口电影更友好了,也有助于更好建设公平竞争、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环境。
三是内容上有了更多的宽容度。从前,不少人总觉得进口片是洪水猛兽、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喜欢“上纲上线”地评价,甚至打压进口片市场。正如你所说,2024年上映的多部优秀进口作品都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先是3月中国台湾影片《周处除三害》上映,引发广泛好评,不少人都惊呼:“这是我能在电影院看的吗?”其效应就是一大批港产片、台产片都排队希望来内地市场获得更好的票房回报和观众评价。到了去年年底,以香港殡葬业为背景的《破·地狱》几乎同步引进内地,上映不到十天,就超过了港澳地区的票房。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电影《鸳鸯楼·惊魂》《异形:夺命舰》《周处除三害》成为2024年三大票房黑马
去年暑期档《异形:夺命舰》上映期间,观众一边互相提示“会吓到小朋友”一边津津乐道。此外还有《小丑2:双重妄想》《角斗士2》《疯狂的麦克斯:狂暴女神》等影片画面恢弘充满张力,让大家充分感受到大银幕在表现追逐、幻想、战争的魅力。当然,也不是都卖座,像《拿破仑》国外卖得不错,国内票房就只有2788万元。所以,还是主要看内容。
我想,好的影片能够在中国市场上收获成绩,一方面是决策者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对普通观众的充分信任,20余年电影改革和开放带给管理层勇气和底气,另一方面也是普通观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提升的必然。
澎湃新闻:从提示“会吓到小朋友”这点来看,是不是也可以说明,观众对电影艺术的认知和宽容度是逐渐提高的,同时市场也有智慧做出相应的调节?
支菲娜:应该说,只要是通过审查进入中国市场的进口电影,就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市场纵深大,一二线城市和五六线城市的接受标准不同,影片内容要尽量照顾到更多观众,因为电影是宽众而不是窄众,越多观众接受越好。
有些影片的部分镜头不符合社会公序良俗,所以要做一些技术处理,让它能更好地为中国市场所接受,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比如前年的《奥本海默》,有场戏是女主角有一个全裸的远景镜头,在影片中国放映版中,导演亲自用后期手段给她穿上了个小黑裙,我带孩子去看的时候就很坦然,而我在香港的同学带孩子去看时就赶紧捂住孩子眼睛。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事实证明大家都能理解和支持。
澎湃新闻:充分的自信才能生发出充分的包容。
支菲娜:是的。虽然2024年票房成绩不如人意,但我觉得2024年中国电影在对外开放上迈出了前所未有的一大步,它是中国电影对外开放的一个新起点和新高度。除了每年统计的那些“在多少个国家举办了多少中国影视节展”等等常规指标,以及刚才说的进口电影市场的变化,还有两个现象具备行业符号学上的意义。

2024年5月,中国电影联合展台在国际村中国馆举办中外电影合作交流会,展望电影国际合作的新方向、新未来。图源:www.cfcc-film.com.cn
一个是去年5月,国家电影局率队参加第7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联合展台”和“中国青年电影之夜”两个官方背景的活动先后亮相,贾樟柯、管虎这两位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参与角逐,还有郑保瑞、陈可辛等港台影人同台。有人说上一次在戛纳见到这么大的华语影人阵容还是2009年。而且这一次是管理部门站在前沿,电影人出自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高度认同,以及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自信,坚定地站在了管理部门的身后。虽然后来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我相信,历史终将证明它们根本不可能构成质疑中国电影发展的阻碍。
另一个就是“《里斯本丸沉没》冲奥”。听参与选片申报的一位老前辈说,原本代表中国内地冲击奥斯卡的是另一部在2024年年初热映的电影,已经走完了国内的所有手续。评审专家们临时决议,撤下来换成《里斯本丸沉没》——我们的目的不是拿奖,而是以此展现中国电影人的担当,展现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以人为本的道义精神。此举得到一路绿灯层层支持。这既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在社会文明和电影行业齐头并进发展的当下,才有可能让这样的一部影片诞生、并在很多看不见的力量支持下,代表中国走向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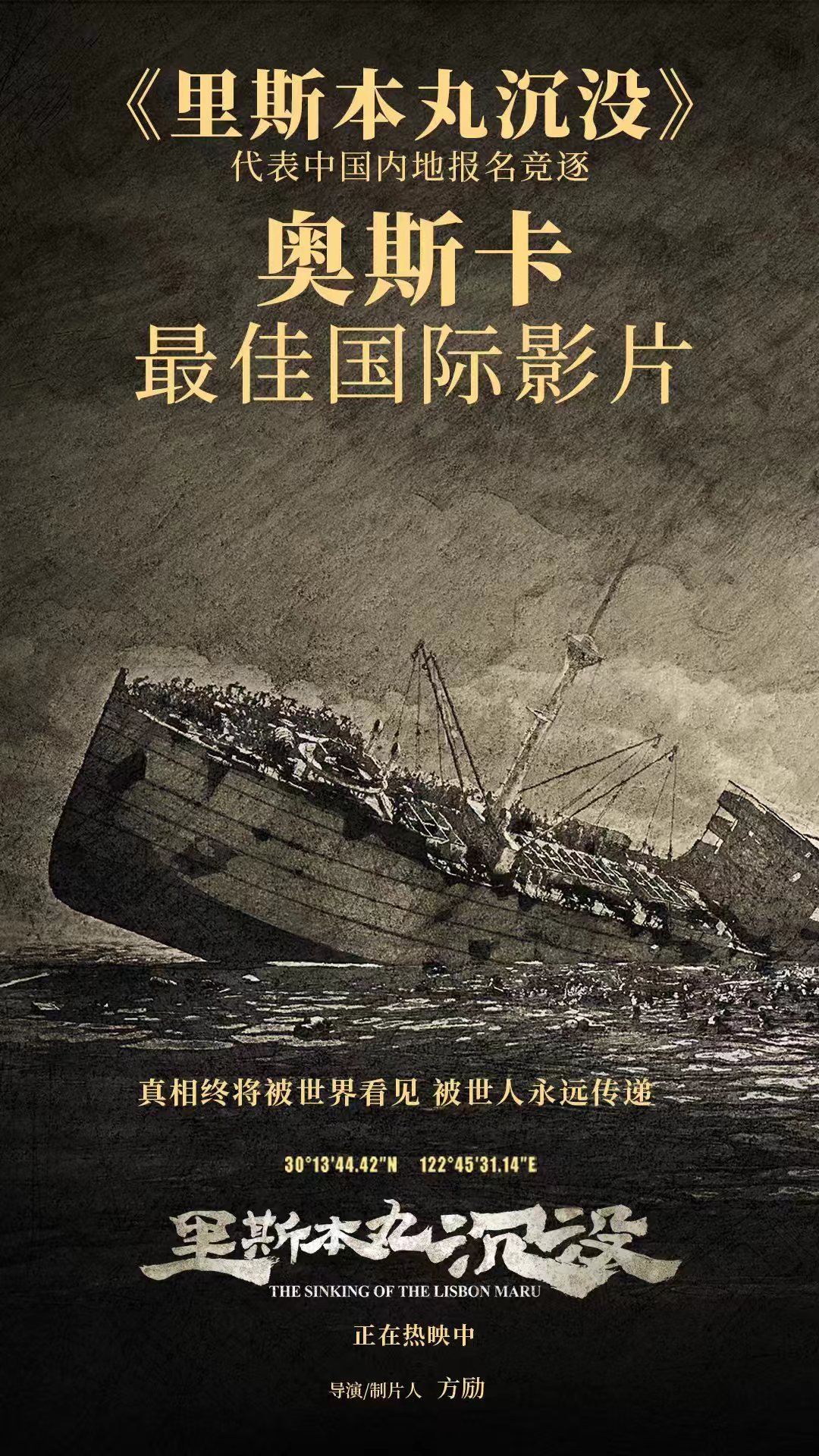
《里斯本丸沉没》冲奥
对内的改革与对外的开放互为表里。中国影视界目前的对外政策框架是2001年定下的,已经不能适应我们在经济、社会、外交上取得的翻天覆地的进步,需要尽快调整。正如有关领导同志曾经指出的“要在开放的气氛中实现中国电影的繁荣”。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们仍然要不断回到加入WTO时电影启动院线制改革、随后启动产业化改革的初心:对内改革、对外开放。2025年,希望中国电影还能在对外开放的道路上继续打开新局面。
电影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
澎湃新闻:展望2025,今年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这无疑是电影的“大年”,你有何建言?
支菲娜:今年春节档,中国电影可谓“全局振奋”。不过,后面还需要加紧投资生产、提升创作水平,切不能透支观众的热情。2024年不少电影人都“限高”了,有人开玩笑说,希望今年能一举改变行业开会大家都只能坐着绿皮火车来的情况。
为观众提供多样化的优秀影片,始终是中国电影的宗旨。我想这一点,120年来从未改变。
澎湃新闻: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的媒介历经百多年,不客气地讲,它也在面对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AI人工智能的冲击,微短剧、电影解说短视频的冲击等等,电影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
支菲娜:电影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这是个好问题,也是个大问题。这次春节档的成绩,可以让那些觉得“中国电影快死了”“电影不如微短剧”的声音消停消停了。但留给中国电影的课题还是很大的。
首先,电影创作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大银幕会让从业人员所有的不认真无处遁形。我想,商业电影分两种,一种是造梦的,一种是写实的,这几年都出了不少佳作,挫折也很多。核心还是,讲好故事了么?编剧、导演、摄影、美术、后期、表演一个都不能偷懒,都得为讲好故事服务。前几年“人傻钱多”,现在观众都被“骗”聪明了,不要败光观众的路人缘。
造梦就要逻辑通畅、画面奇幻、突破想象,《流浪地球》系列、《哪吒》系列、《唐探》系列做得有多好,那些拍不了续集的“大IP”就做得有多差。
写实就要“下生活”,写好人们的痛和甜。2017年,电视剧主管部门在内部总结出了“温暖的现实主义”这个创作趋势,后来经一些学者推广成了学界的热词,也获得了影视界乃至文艺界的更广泛认可。可这两年的一些创作,前怕狼后怕虎,总想既讨好上面又讨好下面,既让专家下得了嘴又让观众迈得开腿,既不想得罪这头又不想得罪那头,既不肯面对历史又不敢面对现实。结果就是给生活加了一层又一层美颜滤镜,变成了“温吞的现实主义”。
经历了2024年的行业低谷,是危也是“机”。一些创作者怎么还能抱持着所谓艺术家的矜持,不肯端正态度去倾听人民群众的喜好和情绪呢?相信人民、尊重人民、追随人民,是电影、也是民族文化复兴的唯一道路。
其次,电影产业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长久以来,我们仅靠票房、人次、票价、场次、银幕数这些指标来衡量电影产业的发展,但电影作为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都仍不足。这个行业统共也就一年几百亿元的票房,恐怕还没有一个顶级大商场一年的产值高。票房能真实反映电影在国民经济、文化传承、文明书写、精神慰藉的价值么?电影是国力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具象化呈现,它对相关行业的带动该怎么统计?通过哪些指标,才能衡量出中国电影完成强国目标?这些问题,不能再盲人摸象。
再次,电影事业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中国电影肩负着重要宣传阵地的责任。2003年以来,国家给予了大量有效的政策支持,这是很多国家电影人都很艳羡的地方。但电影不仅仅是宣传阵地,它是最为市场化的文化产业,也是市场要直接承担代价的事业。我有一点参与宏观的影视管理和宣传管理的浅薄经验,觉得不能完全用管宣传的思维来管电影。实践多次证明,相信市场,市场反而不会逃脱管理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相信市场不是不作为、更不是乱作为。这些年我和地方管理部门打交道很多,那些尊重创作者、尊重市场的地方,行业发展得很好,人才、资金都愿意去。而那些看上级脸色发展行业的地方,就像有关领导同志所批评的,拍了一堆“革命一辈子、票房一万元”的影片。春节档的火热再一次昭示了,电影事业要建立在电影产业的基础上,让观众心甘情愿用脚投票,我们的宣传才有效果。
然后,电影评价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不仅是今年的春节档,这两年电影批评的信用很有危机。不是哪个专家、大V说影片好,观众就会买单。用余华的话来说“最不靠谱的是专家”——也包括我这个专家(笑)。“红包影评”“人情影评”廉价而泛滥。再以高高在上的文化精英主义君临,多少年轻人会听呢?
一些机构的评价体系也是“形势一片大好”,所以被大家长期质疑注水、“没看到开头就猜得到结局”。同时,民间的电影评价信用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来。一些平台既掌控投资、宣发和卖票,又参与排片和评分,对此业界和观众也有不少不满。即便是文艺青年扎堆的一些网站,也被长期指责“有黑水”。所以无论是官方背景的还是民间的,目前看影视界的评价体系和观众的切身体感之间的确是存在距离的,甚至是剥离的。
还有,电影院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有影院经理说本来准备过完这个春节档就关门大吉,但《哪吒2》让他觉得还能坚持到2026年春节档,说出了很多影院“靠天吃饭”的实情。

今年春节期间,有影院创造了单日最高放映场次的记录(一天内最多排了99场《哪吒之魔童闹海》,平均10分钟1场),还出现了多个场次满座的现象。
中国影院的上座率从2015年的18%逐年下降到2024年的8%,而15%是影院的生死线。上座率低,一方面与优秀影片不够多、人们生活压力大和有了更多的娱乐方式有关,一方面也与影院建设速度过快有关。前些年市场发展好,热钱投资建设影院,2016年中国银幕数就超过了美国,位居全球第一。这几年也不断新增,至2024年末突破了9万块,约占全球银幕总量的2/5。说明虽然上座率下滑,市场还没有对影院失去信心。
不过,全国有约1500家影院、9000块银幕是长期不能营业又没有在管理部门注销的“僵尸”,另外还有不少年营业额不足200万元的低效影院“半死不活”。正如刚才所说,好莱坞也好日本韩国也好,都已经转换赛道了,一些管理者还按照上世纪的个人经验,主观认为电影院越多越好,一些经营者还在偷懒躺平等米下锅。所以,要加快影院的高质量发展,淘汰“老破小”和不规范经营的影院,“让该死的去死一死”。
影院不会被VR等新技术替代。社交意义、体验感、声画设备的高品质和密闭空间里对故事的沉浸与认同,是新技术无法取代的。但电影院要有高标准的服务、独特的个性标签和经营策略。我们要充分看到,当下的电影院既是观影空间,也是社交空间,还可以是体验演唱会、赛事、游戏等各种文艺的载体。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电影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借用日前《新闻联播》中的一句话,中国电影应该是“中国经济晴雨表”这样一个存在。几百亿元的产值只是它的表面价值,它在深层次的价值和意义,不能仅仅局限于用票房来衡量。我们对它的信心,不仅仅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的信心,也是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这个信心,自党的二十大以来,我未曾动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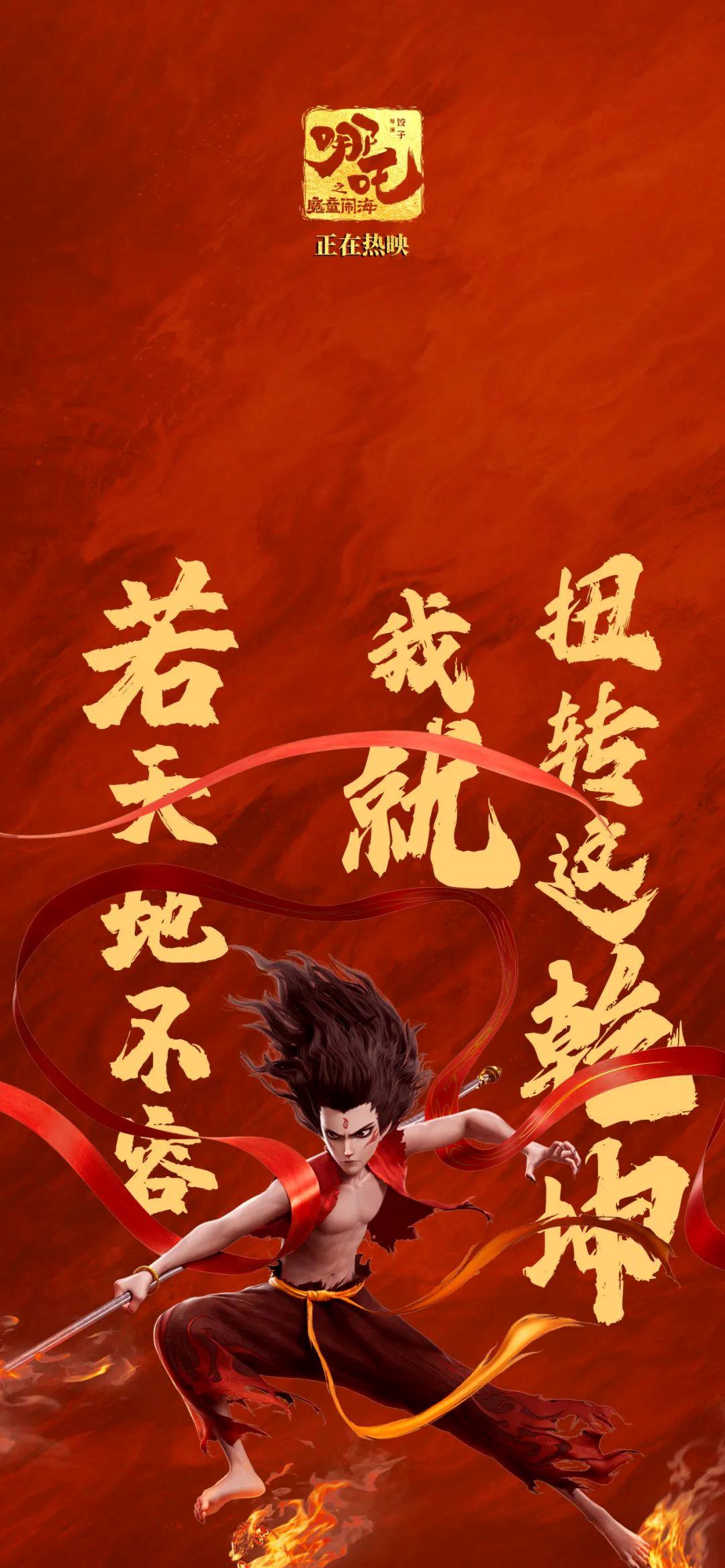
 鲁ICP备2021002543号-1
鲁ICP备2021002543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