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1774-1840年)的画笔之下,自然拥有的魅力不仅限于直接的描摹,也是情绪与灵魂的栖息地。浪漫主义的理念不仅体现于光影与色彩在画布上的交织,更是风景与内心的隐秘共鸣。
时值弗里德里希诞辰250周年之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自然之魂”已于2月8日拉开帷幕,正如艺术家本人所说的——“艺术作品的使命,是感知自然的精神,并以全部的身心去沉浸、吸纳,再以画作的形式将其呈现。”展览通过作品,邀观众品味自然与灵魂的诗篇。

弗里德里希,《雾海上的漫游者》,约1817年。这件作品从未在美国展出。此次,它破例从德国北部的汉堡美术馆借展。
经过漫长的攀登,天气终于放晴,我们眺望远方,凝视着聚集在这片崎岖山岩下的雾气,只有稀疏的草丛从裸露的岩石间探出头来。
然而,当我们透过稀薄的山间空气向外望去,涌上心头的并非狂喜,而是淡淡的忧郁。这幅著名的《雾海上的漫游者》,似乎缺少了一些细节,仿佛被冲刷去了它的独特性。在我们与永恒之间,在人类的理解与宇宙的本质之间,横亘着一层顽固而模糊的白色云雾。
那位身着翠绿色天鹅绒的孤独漫游者,已然成为德国本身的隐喻,并被无数次复制、戏仿。如今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外墙上,这位神情落寞的英雄背对着第五大道,将目光投向远方。
然而,“自然之魂”不仅仅是对这位浪漫主义标志性人物的展示,它还为那些习惯将弗里德里希及19世纪初艺术与平静祥和联系在一起的观众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此次展览由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联合三家德国博物馆策划,共展出80余件绘画与素描,其中包括月光下熠熠生辉的岩石、常青森林中孤立的十字架,以及伫立海岸凝视远方的寂寞德国人。

展览现场
相较于去年德国为纪念弗里德里希诞辰250周年而举办的相关展览,这次展览的规模仅为其一半左右。在德国汉堡的展览,弗里德里希素描中的敏感与细腻令人惊叹不已。他在刻画石块的阴影、叶片的纹理时倾注了极大的关注,使一块原本毫无生机的岩石,化作灵魂的映射。
在大都会博物馆,这种局部与整体间的神奇关联或许不那么明显,但弗里德里希艺术的核心成就依然鲜明可见:他对自然世界那种自发、时而带有神秘感的凝视,以及他赋予一片风景以整个世界观的无与伦比的能力。策展人艾莉森·霍坎森(Alison Hokanson)和乔安娜·希尔斯·赛登斯坦(Joanna Sheers Seidenstein)大力为风景画的价值辩护——这种艺术类型在20世纪一度式微,而今在全球气温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其重要性正再次得到认可。
最为关键的是,这场展览向观众展现了弗里德里希画中林地与草地的动荡——战争、民族主义、宗教、工业化,外部世界正在变革,内在世界亦然:焦虑缠身,怀旧成疾。正是这种内外双重的不稳定——这场心理与现实的“气候变化”——使得弗里德里希与浪漫主义者成为一种精神向导。

弗里德里希,《吕根岛东岸风景与牧羊人》,1805-1806年,棕色墨水和淡彩以及不透明的白漆颜料在铅笔绘制的布纹纸面底稿上、黑棕色墨水绘制的部分框线
1774年,弗里德里希出生于波罗的海沿岸港口城市格赖夫斯瓦尔德——今天属于德国,但当时是瑞典王室的属地。20岁时,他前往丹麦学习艺术。哥本哈根美术学院教授学生如何描绘人体,首先临摹古典雕塑的石膏模型,然后进行真人裸模写生。展览中,一幅他年轻时的自画像——凝视探寻的双眼、紧抿的嘴唇——证明了这些课程的影响深入人心。

弗里德里希,《自画像》,1800年,黑色粉笔绘于布纹纸上
但弗里德里希并不喜欢丹麦的教育,他半途而废,搬到了德累斯顿。这座城市对他有两大吸引力:一是萨克森的艺术收藏,当时和现在一样,都堪称世界上最丰富的之一;更重要的是,这片德国土地已成为诗人、哲学家和艺术家的新兴中心。
他的职业生涯起步缓慢,直到30岁才真正找到如何通过风景画表达情感的方式——他以新兴的棕褐色淡彩技法绘制了一系列广阔而孤寂的画面。展览第二展厅中这些棕褐色充满激情却风格简约的淡彩画让人震撼。太阳在波罗的海上落下,照亮了荒凉海岸的岩石。一位牧羊人在空旷的天空下沿着海岸线行走,天空占据了画面四分之三以上的面积。

弗里德里希,《月升下的阿尔科纳景色》,1805-1806年,棕色墨水和淡彩在铅笔绘制的布纹纸面底稿上、黑棕色墨水绘制的部分框线

弗里德里希,《海上月升》,1835-1837年,棕色墨水和淡彩在铅笔绘制的布纹纸面底稿上、黑棕色墨水绘制的部分框线
在弗里德里希之前,没有人将风景提炼得如此充满忧郁与荒凉。他的作品观察入微,技艺无可挑剔——实际上,弗里德里希的画中几乎看不到笔触,这一点与他的英国同时代人透纳和康斯特布尔的动态构图截然不同。然而,他的视角却极不寻常,画面也从未呈现阿卡迪亚式的田园美景。画中的少数人物,在岩石和大海面前显得渺小得仿佛已被遗忘。

弗里德里希,《晚星》,约1830年
通过这些棕褐色风景画,以及后来的森林、巨石与冰川作品,弗里德里希拒绝了学院派艺术的科学与理性倾向,而是将个体的情感置于首位。对于现代观众来说,这种突破或许难以察觉,因为我们早已习惯将艺术视为个人表达的载体。但在西方文化史上,这种个人化的表达曾是一次剧变——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将其视为浪漫主义时代的标志。他指出,18世纪的法国,尤其是在启蒙运动之后,“个人彻底摆脱了行会、血统和教会的束缚。”而到了弗里德里希所处的德国,“独立的个体开始希望在彼此之间区分开来。”
换句话说,对于这些浪漫主义者来说,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所塑造的公民形象,显得过于抽象和机械化。弗里德里希和他的朋友们所追求的自我认同,必须更具灵性、更具伦理性、更贴近自然。这种自由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必须通过道德和美学的修养加以塑造。

弗里德里希,《两个凝视月亮的男人》,1825-1830年,布面油画。画作描绘了两位男子站在一棵半倒的橡树前,望向夜空中的新月。
这份自由感贯穿于弗里德里希的艺术之中,也正是展览最令人激动的部分——在大自然中不断寻找真实情感,尽管他知道自己永远无法触及世界的绝对真理。
在弗里德里希的许多作品中都能感受到这一点:在那两位朋友的身影中,他们彼此依靠,凝望着半枯萎的橡树上方的新月;在那位张开双臂的女子身上,她面对着日出或日落的山坡;在《雾海上的流浪者》中,他站立在高处,沉浸在迷雾之中。这些德国人不仅渴望自由,更渴望独特性。

展览现场
启蒙思想家将文学视为探索理想世界的工具,而浪漫主义作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却创作出激情凌驾于理性之上的小说与戏剧。启蒙哲学家相信理性通向真理,而浪漫主义者如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则强调理性的局限,将个人体验放在首位。对于那些认为宗教是迷信的启蒙主义者而言,弗里德里希在《海边僧侣》中,却用僧侣的身影来象征那永恒的未知。

弗里德里希,《海边僧侣》,1808-1810年,布面油画。描绘了一个站在辽阔、昏暗、空旷海岸前的小小身影,天空布满乌云。
在弗里德里希的作品中,真正的崇高之处并非山峦或树木,而是自然对画家和观者的主观影响——即风景在历史与时间中如何塑造一个观察者。浪漫主义者称之为“体验的艺术”(Erlebniskunst),即感受凌驾于视觉之上的艺术。对于弗里德里希而言,风景总是一场未知的旅程——既是地理上的未知,也是内心世界的探索。
“陌生人来,陌生人去。”舒伯特的《冬之旅》这样唱道。在展览的尾声,我们看到弗里德里希晚年的棕褐色画作——洞穴、墓地,他放弃绘画后被遗忘的岁月中,这位最德国的艺术家将德国风景描绘成一片几近异域的土地。而这场展览之所以如此契合当下,正是因为弗里德里希始终在风景中保持着一种陌生感——以及他在岩石与松柏之间所寄托的深切渴望——对于上帝的渴望,对远方的渴望。

弗里德里希,《海上月升》,1822年,布面油画
注:本文编译自杰森·法拉戈的展评,原标题为《弗里德里希:在迷雾中寻找方向的孤独漫游者》,展览将持续至5月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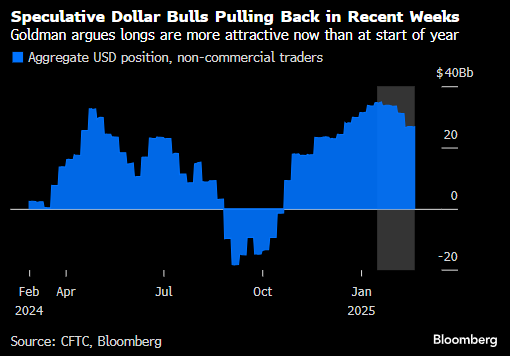

 鲁ICP备2021002543号-1
鲁ICP备2021002543号-1